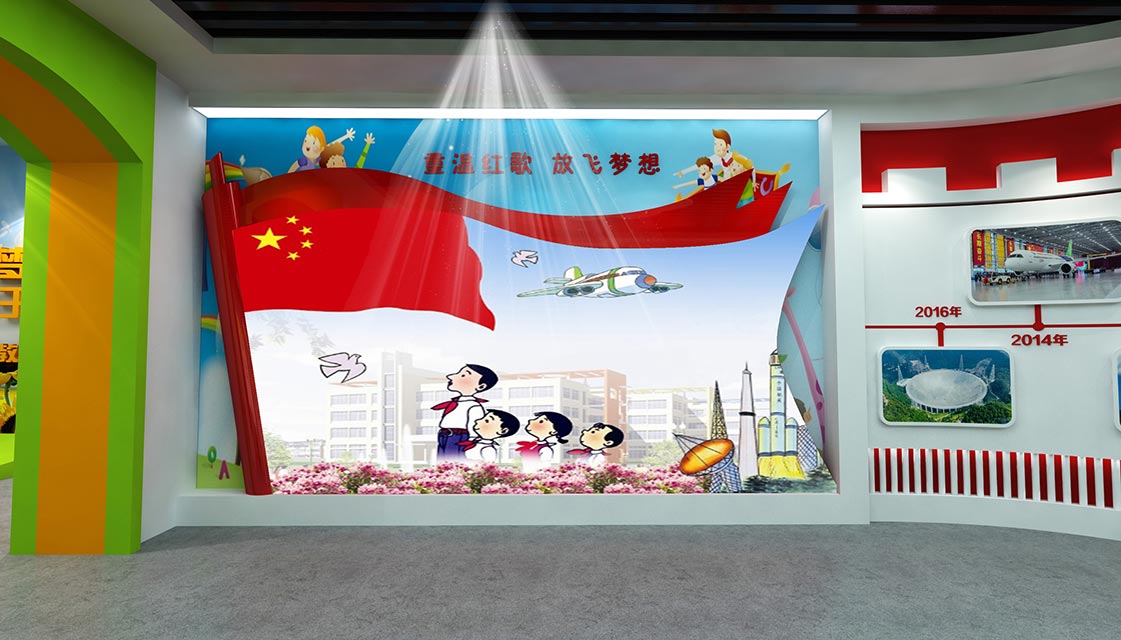為什么仁者便會不憂呢?想明白這個道理,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么樣。
“仁”之一字,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里頭?!叭省?到底是什么?很難用言語說明,勉強下個解釋,可以說是:“普遍人格之實現(xiàn)?!笨鬃诱f:“仁者人也?!币馑际钦f人格完成就叫做“仁”。但我們要知道,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現(xiàn)的,要從人和人的關(guān)系上來看,所以仁字從二人。總而言之,要彼此交感互發(fā),成為一體,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實現(xiàn)。所以我們?nèi)舨恢v人格主義,那便無話可說;講到這個主義,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。換句話說,宇宙即是人生,人生即是宇宙,我們的人格,和宇宙無二區(qū)別,懂得這個道理,就叫做“仁者”。
然則這種仁者為什么就會不憂呢?大凡憂之所從來,不外兩端,一曰憂成敗,二曰憂得失。我們得著“仁”的人生觀,就不會憂成敗。為什么呢?因為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,所以《易經(jīng)》六十四卦,始“乾”而終“未濟”。正為在這永遠不會圓滿的宇宙中,才永遠容得我們創(chuàng)造進化。我們所做的事,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萬里的長途中,往前挪一寸,兩寸,哪里配說成功呢?然則不做怎么樣呢?不做便連這一寸都不往前挪,那可真是失敗了?!叭收摺笨赐高@種道理,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,肯做事便不會失敗。所以《易經(jīng)》說:“君子以自強不息。”換一方面來看,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,幾萬萬里路挪了一兩寸,算成功嗎?所以《論語》:“知其不可而為之。”你想,有這種人生觀的人,還有什么成敗可憂呢?再者,我們得著“仁”的人生觀,便不會憂得失。為什么呢?因為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,才有得失之可言。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,不能明確地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,那一部分是人家的,然則哪里有東西可以為我們所得?既已沒有東西為我所得,當然也沒有東西為我所失。我只是為學問而學問,為勞動而勞動,并不是拿學問勞動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——可以為我們“所得”得。所以老子說:“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?!薄凹纫詾槿艘延?,既以與人已愈多。”你想,有這種人生觀的人,還有什么得失可憂呢?
總而言之,有了這種人生觀,自然會覺得“天地與我并生,而萬物與我為一”,自然會“無人而不自得”。他的生活,純?nèi)皇侨の痘囆g(shù)化。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,目的教人做到 “仁者不憂”。
——節(jié)選自梁啟超《為學與做人》